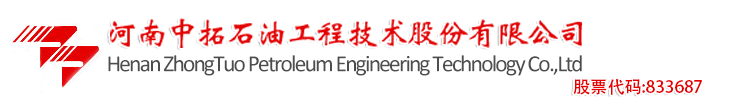曲與直的變奏曲
2014-07-12 10:34:57 點擊:
曲與直的變奏曲
1985年,學(xué)校畢業(yè)時,一個年紀比我小的同學(xué)在我的畢業(yè)紀念冊中留言:有時做獅子,有時做狐貍。
我明白她是一片好心,衷告我更加“成熟”一些,審時度勢,做到“內(nèi)方外圓”。
前些日子,收拾房子,翻出那冊塵封了多年的畢業(yè)紀念冊,看到這句話,心頭涌起許多回憶,我不由笑了。已經(jīng)到了這把年紀,都“知天命“了,卻依舊沒有真正做到內(nèi)方外圓,看來此生秉性不可救藥了。
倒不是說我屬于那種直不愣登一根筋的角色,作為一個社會人,我并不固執(zhí)己見,知道什么話可以說,什么話要說到什么分寸,俗話說:“到哪座山唱哪首歌”,個中的利害我還是知曉,也能夠拿捏得八九不離十。面對許許多多是非經(jīng)歷,我的原則是:寧可委曲,也要求全,所以這些年,幾乎沒有與人發(fā)生過爭執(zhí)和糾紛。
但是,我同樣知道,骨子里的許多東西是難以改變的,曾經(jīng)有一位與我諳熟的同事評價我:喜怒哀樂都掛在臉上。這便注定了我生活中致命的弱點:宛若進了一個園林,沒有影壁墻,沒有曲徑通幽,沒有林木婉轉(zhuǎn),而是一個近乎通透的小廣場,那點亭閣湖泊樹木草坪石塊飛鳥一目了然,可以直面陽光,但是缺少了神秘。
因此,這注定了我的許多經(jīng)歷,也注定了我的人生走向。
曲與直,歷來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比對,人處在一定的環(huán)境中,自然不可能僅以個人的意志為轉(zhuǎn)移,自然要顧及他人的感受和感情,這是一種風(fēng)范,也是處事的一種原則。同時,每一個人都會有做人的底線,只是這條線究竟是“三八線”,還是“麥克馬洪線”,便因人而異了。在我的印象中,大凡成功的人士,多在曲直之間拿捏得當,且在一開始,以曲見長,曲中含直。如我的同學(xué)所說:外圓內(nèi)方。《老子》中寫道的“大真若屈,大巧若拙,大辯若訥”,應(yīng)當是直與曲的經(jīng)典狀態(tài)了。
曾經(jīng)數(shù)次在“直”的苦果面前懊惱,下決心讓自己學(xué)得更“曲”一些,既不傷人,也不害己。比方,在不愉快和憤怒的時候把到了嘴邊的話語咽下去,咀嚼了幾個小時、甚至數(shù)日后再吐出來,我知道,那時候,話語中的鋒芒早已被自己的胃酸腐蝕得卷了刃。但是在一些時候,依舊壓不住那“直”的魂靈,我知道,那是滲透在骨髓里的秉性。倘若過份矯正,搞不好會像那個跑到邯鄲學(xué)走路的壽陵少年,美的姿勢沒學(xué)到,卻連路都不會走了。
不久前,讀有關(guān)一位高層“文膽”的傳記,其中有一句話讓我難忘,書中說那位“文膽”“作為一位政治人物,他懂得,難言之隱只能一個人放在肚子里品嘗”。就在那天晚上,我久久地坐在書桌前,思想直與曲的奧妙。
“路見不平一聲吼”是直,甘受“胯下之辱”是曲,在很多時候,直與曲都是必要的。直,可以以身為薪,點亮生命,照著世界,為人們留下一絲希望:人原本是不必要那么多心機的;曲,則如海洋,容得下天地,把自己的心纏成一個線團,讓他人享受到一份安逸和寧靜。這便是曲與直的辯證:曲是一種境界,直是一種風(fēng)范。
譬如,一根線,繃得過緊會斷,彎得過松會纏,斷和纏都于事無補。當直當曲,就在這樣的“度”前,我與許多人一樣,頗費斟酌。
直到有一日,在博鰲的海邊巧遇臺風(fēng),看到平日挺立的一棵椰子樹在暴風(fēng)雨中順著風(fēng)勢傾斜著身子,既有適度的忍讓與俯就,又葆有了自己獨有的秉直與頑強,我感受到了它的難,更感受到了它的執(zhí)著,那才真真是“直曲自如”,
就在那一天,一棵椰樹作了我的老師。
- 上一篇:國務(wù)院辦公廳關(guān)于加強城市地下管線建設(shè)管理的指導(dǎo)意見 [2014-07-16]
- 下一篇:搶險演練 從實戰(zhàn)出發(fā) (圖) [2014-07-03]